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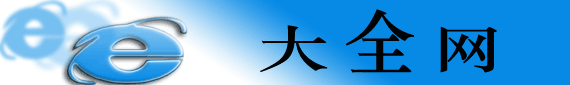 |
我和我的弟弟
一
夜里,或者说凌晨,我被吵醒了。
“妈妈,我要尿尿。”
“给”是姥姥给我的小尿桶儿。
“平,你妈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,你要吗?”姥姥抄着一口沧州口音,干瘪着的嘴角格外地上翘,喜气地对我说。
我下意识地掀起被子,示意姥姥,可以把小弟弟放在我被窝里,屋里笑成一片。
“嘻嘻……,她以为真的放进她的被窝呢。”又是一阵嘻笑。
“她倒是不独。”
我强睁开眼,看到除了妈妈、姥姥以外,还有我不认识的人,她们都喜笑颜开的。
我缩进被子,她们继续着她们的对话。
“起好名字了吗?”
“老大叫留柱,老二就叫留刚。大号回头再起。”
“好,好,留柱,留柱,就是留住了,留刚就更结实了。”
“老大前面有一个哥哥没了,生病没的,留刚是姥姥给起的。”
“哦,唉,活个人不容易呀!”
……
我又睡着了。
到第二天我起炕,妈妈身旁真的有个小弟弟。
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记得是那么的清楚,这可能是我最早的记忆了。
二
西屋炕上有一个精致的被阁子,她给我和弟弟带来许多快乐!
那个被阁子真是好看,她是我们最早触摸到的艺术品,它的正面布满了雕刻,而且都是镂空雕刻,有小柿子、小喜鹊、小蝙蝠、小梅花,还有其它不认识的小花儿,被阁子的下沿的雕刻还有很多讲头儿,听妈妈说叫”桂枝连连“、”喜鹊登梅”什么的,取”富贵如意“的意思,我和弟弟用手指,沿着一个个雕刻图案的边缘,“画”着美妙的“图画”,那是最初的艺术享受,也是最早的绘画模仿,我们还时不时的拿个棍儿在镂空雕刻的缝隙间,穿过来穿过去,现在想想,那都是很精致的雕刻,可称得上是民间文物了,被我们作古着玩儿,真是可惜了。
我和弟弟都是小佬儿,妈妈对我们两个的“胡作非为“总是忍耐有加。
“藏东西”和“爆米花”是我和弟弟结合被阁子最爱的游戏。
仿照“躲猫猫“游戏,我们两个玩儿“藏东西”的游戏。就是在自家的范围内,拿一些小玩艺儿藏在被阁子的阁子或抽屉里,东西越小当然越不容易找到,或是一根草棍儿,或是一分钱的硬币。只要我们一玩儿这个游戏,我们家的炕就遭了秧,为了找到被藏的东西,被阁子里的东西便被我们统统掏出来,抖掕一炕,实在找不到的时候,就把东西往地下扔,妈妈就会喊我们“怎么回事儿,找打啦!“,我们就光着脚,跳下地,把东西扔回炕上,妈妈总会说”小祖宗们,真拿你们没办法。“
我们只管沉浸在玩耍儿的欢乐之中,哪还顾得妈妈的呵斥,也只是冲着妈妈咧嘴笑一笑,投入到我们的游戏中。
“藏东西”是炕遭殃,“爆米花“游戏,就是被阁子”遭难“了。
被阁子下沿的上方并排着三个小抽屉,小抽屉进深长有不到两尺,宽有四寸,高有两寸,我们仿照街道上爆米花的小商贩架势,爆我们的“米花“,一个抽屉当爆米花的”锅“,一个抽屉当爆米花的”风箱“,另一个当填煤的”炉子“,我和弟弟一人拉一个抽屉,卖力地把抽屉拉出推入,推入拉出,极其认真,嘴上配合着一拉一推,起劲儿地模仿爆米花风箱发出的声音,嚷着“起啦夸啦,起啦夸啦……”,小抽屉也伴随着我们欢快的心情,发出悦耳的“
叽啦咣啷,叽啦咣啷……”声,呵,高兴劲儿就甭提啦。
弟弟最爱拉当“锅”的那个抽屉,因为那个抽屉里有当米用的玻璃球,那球在抽屉里被一拉一推,一拉一推的轱辘来轱辘去,碰撞出咕咕噜噜的声音,引发我们对“香喷喷的爆米花”的想象,兴奋得不得了,伴随着抽屉发出的咕噜声,我们嘴里就更卖劲地“酷拉酷拉”助威,还不时地学着小商贩的样子,拿着外地人的腔调,高喊“爆米花爆棒子花……”,“爆米花爆棒子花……”,“大娘,爆一锅吧,一毛钱一碗,不贵。”我们还不时地在“锅里”抓一把“米花”放在嘴里,发出“喃喃,喃喃”的吃米花的声。
米花“吃“得很香,抽屉真是遭殃,我们不管那一套,高兴着呢。
三
我和弟弟同心协力,发挥想象力,祸祸着家里。
“藏东西”“爆米花”是炕上的活儿,“开火车”、“骑大马”就是地上的事儿了,妈妈不让我们到胡同里玩儿,说是危险。
“开火车”、“骑大马”的道具就是家里的小板凳、马扎儿和坐墩儿等。那时候每家少说有四五个孩子,人口较多,冬天一家人坐在炕上,围着饭桌吃饭。夏天坐着小凳子、马扎儿、坐墩儿等能坐的东西,围着饭桌吃饭,因此,不愁没凳子玩儿。那坐墩儿多是麦秸编制而成,有的人手巧,做出的坐墩儿简直就是工艺品,有方的,也有圆的,可好看了,要是放在现在人们的眼里,那就是工艺品,说不定还可以给国家挣外汇呢。
在院子里玩儿“开火车”、“骑大马”可以信马由缰,我比弟弟大,当然总是比他快,他落后于我时,经常是抱起板凳往前跑,我只是说他耍赖,但也不着急,但,小伙伴们来我们家玩儿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小伙伴们来玩儿的时候人多,经常性地进行比赛,比谁的“火车”开得快、比谁的“马儿”跑得快,每当这时,我就尽量搅合的小伙伴们制定比赛规则不平等,总的意思就是让弟弟先行一步,或是想法儿横在别人前面,让弟弟快行,倒也没人跟我计较,我的小伙伴都比弟弟大,都让他三分,真是“平等是相对的,不平等是绝对的”,亲情大于友情了,这人打小就有不平等的潜意识,看来”腐败“根源在这儿呢。
最有意思的是玩儿“格斗”。人多,也不分“敌我”阵营,骑在小板凳上,满院子的胡追乱撞,那时的我也顾不上弟弟了,专心找“敌人厮杀“,真可谓:腿借蹬力,人借“登”威,威风凛凛,喊声阵阵,把院子里的地都屠戮起来,弄得满院子爆土扬长,至于我们每个人,土头土脑的,鞋上和裤脚弄得都是土,没办法,战斗吗,就要豁的出去!至于胜与不胜,反正都喜气洋洋。
相对于在院子里的“万马奔腾”,在屋里玩儿就“文静”多了。
在屋里玩儿的时候,把凳子、马扎儿、坐墩儿排成一溜,有车头、车身和车尾,司机、乘客的和乘务员就那么几个人,都是“兼职”的,如果没有小伙伴儿们,我和弟弟就“身兼数职”。
“同志,是到杨台的车吗?“
“同志,是到军粮城的车吗?“
“同志,是到北京的车吗?“
“同志,是到上海的车吗?“
“同志,是到唐山的车吗?“
“同志,是到沧县的车吗?“
……
这时候最考验我们的地名知识了,“乘客”尽自己的可能,把知道的地名都报一报,“司机、乘务员”也紧着力儿的启发、补充地名。当然,开车的和乘务员也不厌其烦,只要你能报出的地方,它都能到达。
“请给抱小孩儿的让个座儿。”
“大婶儿,您坐这儿。”
“好闺女,谢谢你!”
“刚上来的请买票。”
“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,请您坐稳。”
“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,请您扶好把手。”
要论文明礼貌,非我们莫属了。
“呜呜呜!……”“轰隆隆,……”
“火车飞,汽笛响,欢欢喜喜把歌唱,……”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伟大领袖毛主席,指引我们向前进。……”
火车承载着“满车“的欢乐和歌声,“驶向远方”。
哥哥姐姐有时就开我们的玩笑,说“呵,这车开得倒蛮快的,坐地不动,绕地球的距离,一会儿就到,真是‘坐地日行八万里’。”
我们不懂得这是幽默,只是回敬他们“愿意,你们没玩儿过吗?“
四
弟弟大一些了,妈妈要到外面干活去,做临时工了。
“妈妈,您能不去上班吗?上班多累呀!”我和弟弟带着哭腔哀求妈妈。
“妈妈得去挣钱,哥哥姐姐都要上学,光指着你爸爸挣钱,哪够用的。”
“哥哥姐姐小的时候您上班吗?”
“不去,那是因为家里可以搞点儿副业,打草绳,编鱼篓儿,现在不行了。”
“大婶家的二哥三哥,八娘家的小利子和二哥不是都不上学了吗?不让哥哥姐姐去上学不就行了吗?”
妈妈一脸严肃地说“那怎么行!不管别人家,你们都得上学,爸爸妈妈累点儿也要供你们上学,知道吗?”妈妈说得很坚决。
留不住妈妈,我和弟弟都很失望。
妈妈从此再也没有停止过临时工的工作,直到我师专毕业,她老人家60岁才“退休“,“退休”两个字之所以带引号,因为临
时工没有退休这一说。妈妈结婚早,身体自然是受过“磕塴(beng)儿”的,因此身高只有1.5米多一点,可临时工没有轻松的活儿,夏季时给供销社做西瓜搬运工,冬季前到煤厂跺煤坯,抬煤球,后来到供销社酱菜厂做咸菜,机米厂缝麻袋,草袋厂编制草袋子、晾晒厂晒图版等等,样样都不是轻松活儿,妈妈一定很累。
姐姐哥哥们都上学去了,我和弟弟就成了家里的“顶梁柱”。
“好宝儿,给妈妈喂喂鸡。”
“好宝儿,下雨了把怕雨淋的东西收拾到屋里。”
“好宝儿,出门时要锁门,回家后要插门。”
“好宝儿,尽量在家里玩儿。出去玩儿的时候,不要走远,这个表上的长针走到这儿,短针走到这儿,我就回来了。”
妈妈很不放心地嘱咐着我们。
“噢。”
我们使劲儿地点着头。
我是姐姐,我觉得妈妈的嘱咐是对着我的,我感觉“使命”重大。
我和弟弟虽然不知道妈妈在外工作有多累,但懂得妈妈会比在家辛苦。因此,我们努力做一个好孩子,我和弟弟不管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打,怎么闹,只要快到妈妈回来的时间,我们都会收兵,结束“战争”,收拾好情绪,尽量在妈妈回来前把玩儿乱了的屋子收拾收拾,让妈妈回家后看到我们是好孩子。
一天,我们两个突发奇想,给妈妈把中午饭熥好。说干就干,妈妈一走,我和弟弟就把“稻皮儿”和柴禾都堆到灶台前,把铁篦子插入灶内,把风轮安好,准备热饭。
这一天的上午过得好慢,我和弟弟一会儿盯一下表,一会儿盯一下表,好不容易挨到到点儿,我和弟弟满怀希望地点火,开始热饭。刚点着火,妈妈就进了家门。
我们一反常态地问妈妈,“您怎么回来那么早?”
“到点了不回家,干嘛呢?”
“给您热饭!”我们兴奋地说,心里等着妈妈表扬。
“谁让你们热的?”妈妈有点儿着急。
……
我和弟弟都有点儿懵。
过了一会儿,妈妈缓和了语气对我说“火是不能随便点的,出事怎么办?想学也得等大一点儿再学,大人在家的时候学,在家把弟弟哄好就行了。明白吗?”
“明白了。”我答应着,使劲儿点点头,好让妈妈放心,其实不怎么明白。
五
有我们不用学就能帮到妈妈的事情。
一天狂风大作,我和弟弟还在陈八娘家门口玩儿,陈八娘对我说“这么大风都快下雨了,你们还不赶快回家!”说时迟,那时快,雨点砸了下来。
我和弟弟赶紧回家,把认为怕雨淋的东西抢进屋里。
我们上炕,趴在窗台上,隔着玻璃看外面下着的大雨。我印象中,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雨,一会儿的功夫,院子里的雨就有半尺深,那雨水可着劲儿的朝院子里的阳沟眼儿处奔,到阳沟眼儿的雨水又使劲儿往外挤,生怕出去慢了进到我们屋里似的,谁也不让谁。
“雨真大!”
“雨太大了!”
“雷真响!”
“嗯,像打炮似的!”
“打炮也没有这么响!”
“亏得咱俩跑得快,要不全都淋湿了!嘻嘻……”。
“咱妈妈说,淋湿了容易发烧!”不知到什么原因,我特别害怕发烧。
“咱妈妈没有带雨衣!”我和弟弟几乎同时喊叫起来,感觉妈妈处在了危险之中,我们恐惧起来了。
“我给咱妈妈送雨衣去!“我和弟弟几乎又是同时喊出来,而且都急着下炕穿鞋。
“我去!”
“我去!”
“我是男的!”
“不比你大!”
“再不去,妈妈就要挨淋了!“
“所以我去,我比你跑得快!”我说。
弟弟被说服了。
我找出雨衣夹在胳肢窝里,去给妈妈送雨衣。
“你怎么办?”
“我是男的,我不怕!”弟弟语气坚定地说
“三姐,你快点儿,但别摔倒了!”弟弟的话充满矛盾。
“哦。”
妈妈在大约三里地的机米厂上班。
雨,太大了,放眼望去,白茫茫的,个别地方水很深,都到我没过了我的膝盖到大腿了,我在恐惧与勇气中狂奔……。
我赶到机米厂门口时,雨小了些,我怯生生地向门口的传达室内张望,看门的看到了我,让我进到屋,我说明是给妈妈送雨衣
的。
“在那个车间上班?“
“……”
“干什么活儿?”
“……”
“都不知道,只知道我妈妈叫张宝华!”
“机米厂大了,光大门就有三个,这是一门儿,还有二门儿和三门儿呢,你什么都不知道,怎么送?”
人家不让进,也不给传,真恨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。
只有在一门儿的道边上等着妈妈。
“雨不下了,你回家吧”。
“一会儿再下怎么办?我等我妈妈下班”。
“得会子才能下班呢,再说,你妈妈不一定走这个门。”
“那也等。”我出了传达室,站到了对着一门的马路对过。
妈妈下班了。
“好孩子”妈妈说,阿姨们也说。
“弟弟呢?怎么能把弟弟一个人放在家里!”妈妈一说,我立时紧张起来。
回到家,进了屋,弟弟抱着斧子睡着了。
“抱着斧子干嘛?”
“砍坏人的”弟弟的话充满了勇气。
“砍不了坏人还不得让坏人砍了你”,我们都笑他的想法可笑,弟弟翻着眼皮白了我们一眼,抿着嘴,没吭声。
弟弟虽然没能争过我去给妈妈送雨衣,但弟弟拿着斧子保卫着家!
弟弟是真英雄!